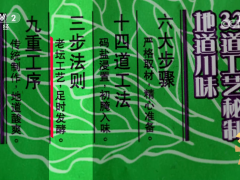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呼吁:“要加快推进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的布局,重点关注新污染物的环境暴露与人群健康效应,确保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能够真正转化为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
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这是“新污染物治理”连续第四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难以降解、长期残留,被称为“永久化学品”,成为全球环境科学领域的重大挑战。
▎PFAS无处不在,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江桂斌院士提到,“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的新污染物种类很多,因为我们的生活与化学品的使用息息相关。例如,PFAS因具有疏水和疏油的特性而广泛用于不粘锅涂层、衣物防雨涂层等。”然而,这种“奇迹材料”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挑战。由于其极高的化学稳定性,PFAS难以自然降解,一旦进入环境,便可长期残留,并通过水体、土壤和空气不断积累,形成全球性污染。
研究发现,PFAS不仅已被检测到全球河流、地下水、食品中,甚至在人血液样本中也存在,其中某些化合物的半衰期可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新污染物整体上具有广泛的毒性,包括神经毒性、发育毒性、内分泌干扰、免疫毒性等,这些毒性表现都是在分子尺度和种群尺度上评估生态健康风险的关键靶点。”江桂斌院士指出,“但由于其长期低剂量暴露的特点,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其具体的健康风险。”
当前,有研究发现PFAS暴露可能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包括癌症、肝功能异常、免疫系统紊乱、内分泌干扰等,甚至可能影响胎儿发育和儿童健康。然而,由于其低剂量、长期暴露的特点,传统毒理学评估方法难以精准量化其危害,因此仍需深入研究其健康风险机制。
▎PFAS治理的三大挑战:源头、过程与末端
面对PFAS的广泛污染,全球范围内已开始加强管控。2023年2月欧盟提交了10000多种PFAS化合物的限制提案,美国多个州已出台法规限制PFAS在消费品中的使用等。在我国,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也在2022年联合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将PFAS列为重点治理对象。江桂斌院士强调:新污染物的治理需要“源头控制、过程减排、末端治理”三管齐下。
源头控制是最有效的防治策略。 江桂斌院士建议借鉴“《斯德哥尔摩公约》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管控经验,即基于基础科学先行原则,探索在PBT(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高毒性)特性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促成政府、工业界、科学界在需重点管控污染物种类上达成共识,再基于工业类型摸清排放清单、设立管控标准。”而目前,由于PFAS广泛应用,且部分行业尚无完全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过程控制仍面临较大挑战。另外,科研人员所探索的膜过滤、活性炭吸附、高级氧化等技术的成本高昂,且“鉴于环境介质的复杂性,完全清除新污染物是不现实的,”江桂斌指出,“我们只能针对特定污染严重区域进行治理,同时加强长期监测。”
▎科技创新与政策引导,共同破解污染难题
PFAS污染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治理不能单靠单一措施,而需要科研、政策、产业等多方面协同推进。
江桂斌院士建议,“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构建环境暴露-风险评估-健康效应-防控理论体系。”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合成生物学新毒理模型等先进技术帮助研究人员更快速地筛查高风险新污染物,预测其环境行为及毒性,为监管和治理提供更精准的科学依据。江桂斌院士的团队目前也在以关键毒性靶点为线索,利用AI等技术推进污染物筛查和环境赋存解析;同时,环境毒理学研究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也在系统加强,以助力发现新污染物的毒性靶点、解析毒性通路、理解健康效应。
此外,“应加快推进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及平台建设,”江桂斌院士强调,“构建‘水-土-气-生’新污染物立体监测网络,提升陆海统筹的环境科技创新的支撑和技术装备研发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体系。”
新污染物治理不仅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关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与全民健康息息相关。需以“科学基础战略”为先导,通过动态优化研发任务、主导国际数据智库、完善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将科学认知深度融入社会治理框架,为高水平保护与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