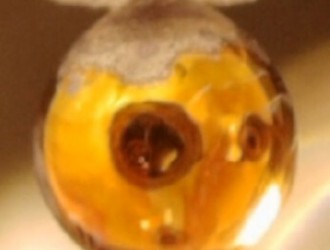本文原由美国布尔茅尔学院化学教授Michelle Francl撰写,2020年3月发表在自然化学期刊上,生命科学前沿编辑部编译。
看到推特上茶包形状对泡茶效果颇具有影响的帖子时,我想起了第一次遇见Wilhelmina Green的场景。
那是在费城的奥斯默图书馆。彼时,我正在阅读化学新闻,边品着自己钟爱的茶。开个玩笑,这当然是我幻想中的一厢情愿,毕竟我既不可能在奥斯默图书馆阅览室喝到茶,更不可能邂逅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Green。
我翻出了Green在1885年写下的论文《泡茶》,论文里是她对红茶冲泡的化学分析,深入而细致。Green发现,人们对茶浸液的化学成分、泡茶过程的化学反应动力学和提取所需化合物的最佳冲泡方法知之甚少,这让Green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决心弥补这一空白。
重读Green的论文以及推特上关于茶包形状的讨论帖,启发了我要查阅文献,来一探如何泡一壶好茶。
现代文献对茶叶冲泡成分和动力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21世纪的化学家对泡茶又有多少了解呢?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少。1946年,Orwell在其短文《一杯好茶》中,关于泡茶给出了11条建议。我在这里提供其中的7个,也许你并不会之所动,但这些建议都有科学文献的支持,绝非无中生有。

热水,开水,谁适宜泡茶?
沸水能够带出茶中的咖啡因。咖啡因苦涩,并能阻断腺苷受体,让你保持清醒,我常用一杯茶开启新的一天,亦源于此。Green的文章表明,100℃条件下短短5分钟,咖啡因几乎都能被提取出来,而单宁酸(浓茶伤身的最主要物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Spiro和Siddique在研究泡茶动力学时也发现,茶黄素和咖啡因在较高的温度下更容易被提取出来。
奶茶,柠檬茶,谁更有利健康?
无数的数据表明,添加牛奶会降低茶中抗氧化物的含量。如果你愿意,可以用柠檬来补充维生素,或者用来增加些许甜味。
奶和茶,谁先入杯?
先倒牛奶还是茶,从科学的角度,仍然是悬案一桩。Orwell从常识的角度认为,后加牛奶可以更加精确地目测出茶与牛奶的比例,这与品茶师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皇家化学学会的Stapley对此颇有微词,他担心,将牛奶加入热茶中会使蛋白变性。国际标准化组织认为先倒茶,茶凉至80℃以下再加牛奶,是较为妥善的做法。
凉茶,需要加热吗
“茶凉,尤劣于亡故。”
Mikhail在《伊拉克之夜》的诗中,如是说,
凉茶上面的浮垢,是有机物、钙和镁的碳酸盐。这种漂浮着的浑浊称为乳析,它是茶水冷却时低溶解度化合物沉淀的结果。使用蒸馏水(矿物含量少)和添加螯合剂可以减少乳析。也可加入柠檬形成可溶性的柠檬酸盐,再离心将残余物取出。
泡茶,宜反复吗?
冲泡5分钟后,茶叶中剩下的咖啡因不到5%。茶黄素和茶红素也大量减少,反复冲泡徒劳无益。
茶中含有重金属?
茶是氟化物,也是铝和锰的重要饮食来源。茶浸液中确实可检测到铜、铬和铅。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金属似乎不具有生物利用度,所以端起茶盏,喝吧。
茶包形状有影响吗?
茶包形状对泡茶效果真的颇具影响吗?对此,我绝不相信:忘记那些花里胡哨的茶包吧。相信Jagyani和Ndlovu也会举手认同,因为他们认为,尽管茶包的材质和大小很重要,但形状真的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事实上,散茶入杯,你会得到更多的咖啡因和抗氧化物。
茶,素来为人所熟知。茶中又有大量的化学物质。弄明白茶中的化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个人观察与所学化学知识之间的联系。
每当我向茶汤中挤入柠檬汁,就会想起我的基础化学老师Sherry Rowland教授在期中考试时提的第一个问题:“加入柠檬后,茶的颜色会明显变淡,为什么,请给出适当的化学方程式”。依然记得看到这道看似无厘头的问题时的恐慌,但我还是冷静了下来,给出了正解,并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化学家。
一冲一泡间,茶,自有其力量。
内容来源:
Francl, M. A chemist’s cup of tea. Nat. Chem. 12, 319–320 (2020).
扩展阅读:
喝茶或可有助于防治新冠肺炎?
茶叶,是中华文明馈赠给世界的重要礼物之一。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直到现在,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一直以来,茶不仅局限于作为人日常饮用的饮品,还在清热解毒类中药的经典名方之中。曾有古史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说明“茶”在长久的食用过程中,人们越来注重它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的“药”用之性。
《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此茶之功也。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是从茶叶中萃取的儿茶素类化合物的主体成分,现代研究发现,EGCG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抗病毒、抗癌、抗福射损伤等多种天然生物活性。
以往研究表明,EGCG可通过直接破坏病毒颗粒、阻断病毒与细胞受体结合、抑制病毒生物合成等环节发挥抗病毒作用。目前已知EGCG对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柯萨奇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艾滋病毒和SARS病毒等均有抑制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李华教授、沈阳药科大学无涯创新学院陈丽霞教授和军事医学研究院李行舟研究员等合作发表在《药学学报》英文版的文章“Analysisof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SARS-CoV-2 and discoveryof potential drugs bycomputational methods”通过计算机筛选方法首次发现EGCG能够与新冠病毒关键蛋白酶—木瓜样蛋白酶产生很强的相互作用,另外EGCG与新冠病毒受体ACE2(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也有很好的亲和力。
后续团队又发现EGCG与新冠病毒治疗的潜在新靶点—人类弗林蛋白酶,也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和既往的研究数据,将EGCG列为治疗新冠病毒的潜在候选药物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此前,就有研究发现,EGCG和EGC 对于引起非典的SARS病毒关键蛋白酶—3C样蛋白酶有非常好的酶抑制活性,而且分子对接表明,EGC能够与3C样蛋白酶活性口袋中多个氨基酸残基产生氢键相互作用。
最近,云南农业大学盛军教授研究团队在分子水平上发现EGCG能够与新冠病毒S蛋白结合,阻止S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从而阻止病毒进入宿主细胞。此外,EGCG对于已经结合ACE2的S蛋白,有促进两者解离的效果,目前此研究成果已经在昆明市第三医院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用于临床辅助治疗(云南卫视晚间新闻2020年2月28日报道)。
此外还有两项研究,也发现EGCG与3C样蛋白酶和木瓜样蛋白酶有很好的结合亲和力。这些结果都说明,EGCG可能通过靶向新冠病毒一个或多个关键酶,阻止新冠病毒蛋白成熟以及RNA复制,从而达到抑制病毒的效果;另外也可能作用于人ACE2或者弗林蛋白酶从而阻止新冠病毒进入宿主细胞,以上发现为EGCG作为潜在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4700多年的饮茶文化,已经直接向我们证明了食用EGCG等儿茶素类的安全性,另外,2006年美国FDA批准了茶叶提取Veregen(包括EGCG、EGC等多种茶多酚)用于局部(外部)治疗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的生殖器疣,这是FDA批准上市的第一个植物药,也同样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证明茶叶提取物的抗病毒活性和安全性,以及药食同源在现代药物研发模式中的可行性和潜力。
由于Veregen是局部外用的药物,目前已知口服ECCG的生物利用度较差,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体内抗病毒药物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其活性和机制,并解决口服生物利用度以及药代动力学等问题。虽然如此,也已有研究表明,EGCG能够在动物体内模型水平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另外,利用纳米颗粒的药物递送系统,可以大大提高EGCG的生物利用度,改良它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将茶叶提取物做成喷雾剂直接作用于呼吸道系统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苗和新药研发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在没有经过长期的安全性评价的新药也无法上市,药物的安全性评价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对于新冠肺炎这种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发病急,致死率不低的疫情,等待全新药物是有点令人着急的。此时,从安全性非常好的药食同源中寻找潜在的防治药物是最直接、耗时最短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目前来看把EGCG或者茶叶提取物作为新冠肺炎治疗的候选药物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合理和可行的。对于临床治疗具体需要的剂量以及给药方式,需要对EGCG或者茶叶提取物的作用机制、药物递送系统、生物利用度和药代动力学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我们平常饮用的茶里,绿茶的EGCG含量最高,一杯200ml绿茶(如杭州龙井)约含142mgEGCG、65mg EGC、28mgECG、17mg EC等茶多酚。考虑到绿茶中的咖啡因和茶碱等物质含量也较高,它们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不适合肠胃不太好的人长期大量饮用,另外它们还有较强的中枢兴奋作用,可能不适合某些人。EGCG含量略低而咖啡因含量较低的白茶(如福鼎白茶)、乌龙茶(如大红袍)等则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从EGCG相对较低的口服生物利用度来看,平常剂量的饮茶也可能不足于达到抑制新冠病毒的浓度,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确定是否经常喝茶的人更不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或祸患重症。因为茶叶中还含有咖啡因和茶碱等中枢兴奋物质,过量饮茶来预防新冠肺炎可能并不可取,适量饮茶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生活方式。
在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中传统中医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明确详细地指出了不同程度、不同症状的患者根据不同的方案进行辩证治疗。其中也包括很多药食同源的成分,例如:化橘红/陈皮、杏仁、山药、生姜等。
来源:文章来自生命科学前沿。